日影憧憧的证词——读许小鸣的《我和我的抗战》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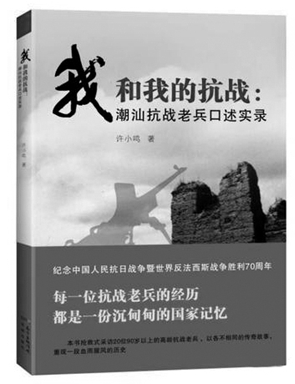
许小鸣/花城出版社/2015年7月
“卢沟桥事变”之后,许多热血青年纷纷从潮汕走出去参加了抗战中的大型战场。像杨汉威、林乔佐这样的青年投笔从戎,浴血沙场。而当年的潮汕战场羊铁岭、大脊岭等战略要地,也是日军踏足岭南以来,最头痛的地方,潮汕的血性也可见一斑了。
这本书有一个副标题:潮汕抗战老兵口述实录。从老兵的作战经历到战场的背景资料,很难想象,完成这种采访,这种写作,需要一颗多么强大的心脏。如此莽荡的人事,于作者、于读者而言,不仅仅是慨叹,还有挥之不去的锥心之痛。70年前的抗战,老兵们以热血铸造国格与军魂。70年后,许小鸣用3年的时间,完成了数十个抗战老兵的采访,泪成此书。拿她的话说:“写完老兵们的抗战,我自己的抗战也胜利了”。
许小鸣是如何讲述老兵们的抗战呢?
稍有文学史知识的都知道,战争题材文学作品,围绕民族国家现代性的想象以及大众对英雄的期许,与政治意识形态基本上是同构的。直至上世纪90年代,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,道德伦理随之嬗变,这一时期的战争题材文学,与大众文化、商业心理多有合谋。看起来是更加个人与自由,事实上,大多数作品天马行空之后,并没有落在大地上,而是臣服于商业的舞台。战争,这个人类最可怕的怪兽,在他们笔下,成了娱乐的大本营,人的悲剧性荡然无存。
许小鸣的纪实,显然是对以上情势的反拨。她通过书中的二十位老兵,多半穷困潦倒、晚景凄凉。如黄俞鸣,追随孙立人将军参加淞沪抗战、南京保卫战、远征缅甸,因离乱而流落他乡。迟暮之年,连回老家看看的愿望都是奢侈的。黄明、罗春晖等人跌宕起伏的命运,记录日本侵略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深重苦难;通过谢爱有、徐秀专等人不期然而然卷入战争,并造成了无法回避的悲剧命运之书写,建构了更加宏阔的英雄观。
英雄不问出处,英雄也不问动机。无论是因为逃荒要饭、升官发财还是为民族大义,只要不投敌不卖国,都算得上民族的脊梁。让人嘘唏的是,抗战胜利后,国共战争烽烟再起。身为“国军”,命运多舛就在所难免了。他们注定了被时代的列车碾压、抛弃。“我只杀过日本人,我没有杀过中国人,我不是罪人。”躺在病床上的老兵谢茂强反复说着这句话。本该是英雄的,却因局势的变化,失去身份的正当性,因而如野草浮萍,数十年风雨凄苦,默然承受。
许小鸣是有悲剧意识的作家。《我和我的抗战》写生死一线的战争风云,写波诡云谲的政治运动,写承平岁月里的精神困惑。但是,她不指控、不纠结于时代的语境,而是把英雄群像还原成普通的个体。基于战争进程、时代转折带来的悲惨境遇,以及个人命运的浮沉,揭示战争前后,生命里的不可思议。
她还有一颗“不忍之心”。每每写到命运的恶转,此前的酣畅淋漓立马收住,顾左右而言他,此间的省缺,深意其中,恻隐俱焉。一介书生、一枚女子的许小鸣,能够精雕细刻战场上的血肉迷糊,却不忍触动老兵的无奈与无告。这样的“不忍”是令人尊敬的。它保全了老兵的荣光与尊严,抚慰了他们的哀愁与疼痛,也让读者看到离乱、纷争的世界里,还有值得珍重的东西。
(时间:2018年12月2日 来源:番禺日报 作者:舒然)

